何林:缅甸“胞波”的文化逻辑
【作者简介】何林,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摘要】作为一个缅人对汉人专用的称呼用语,“胞波”不仅反映了缅、汉两族的亲密交往,而且在缅甸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和逻辑,甚至深刻地影响着缅人对于缅、汉两族乃至中缅关系的想象、认知及态度。
【关键词】胞波;缅甸文化;中缅关系;华人华侨
引言
在汉语语境中,“胞波”主要指中缅国家间专有的称谓用语,并已成为表示两国友好关系的象征符号,而在缅语及缅甸文化中,其原生词语(Pauk Phaw) 首先是缅甸缅人对旅居汉人(华侨华人)专用的亲切称呼,反映了缅、汉两族的亲密交往及汉人于缅甸社会的整合。“胞波”及其所指之“同胞兄弟”,在缅甸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及逻辑,甚至是缅人早期国家意识建构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支撑点”。缅甸经典编年史《琉璃宫史》中关于“太阳神之子与龙王孙女‘蛋生’中国王后和缅甸国王”的传说与“胞波”一词内涵相近,故在当代中文网络中被引用为“胞波”的文化来源,而这一传说的出现绝非偶然。作为一部重要的史籍,《琉璃宫史》以宗教(佛教)、民族(缅人)、国家(缅甸)“三位一体”为中心建构了缅甸早期国家意识的基础:缅人为佛陀的子民,是虔诚的佛教徒;“古代缅甸国王来自古印度佛陀所属的高贵的释迦族乔达摩种系”;缅人历史上建立的三大统一政权,是值得荣耀的国家实体及当代缅甸的历史基础。此外,缅人通过古代缅甸与中国之“同胞”关系的“想象”成功为王国政权的合法性、国家民族的独立性及缅中“平等关系”等需求建构了文化基础,并在内部话语体系中进行表达——《琉璃宫史》事实上也扮演了特定时期话语工具的角色。《琉璃宫史》记载了缅人对国家历史与文化的想象、认知及理解,一个多世纪以来形成并持续支撑了缅人强烈的宗教、民族与国家自豪感、归属感及责任感。在两国悠久而频繁的交往中,中国常常作为缅人国家意识建构的参照而见诸缅甸史籍。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即《琉璃宫史》成书的时代,缅人开始以专用词语“胞波”称呼他们的汉人邻居——缅中“同胞”观与缅汉“胞波”关系分别在“同一现象的不同抽象”的(缅甸) 文化与社会结构中相对应。近代缅英战争中的惨败及英国殖民统治的屈辱使缅人的民族与国家意识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在当代缅甸国家民族意识中,《琉璃宫史》仍然是重要的思想来源,而与中国的交往也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新型中缅关系的建立而翻开了新的一页。
1、胞波传说
一、缅人早期的国家意识
(一)《琉璃宫史》的建构
有关缅甸的历史研究,中国古典文献记载及近现代史学论著较为全面,自然具有了中国的视角;西方的研究,如影响较大的哈威《缅甸史》等,“材料丰富,考证精确,但毕竟是站在英国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立场的英国人写的…… 特别是牵涉到东方与西方关系,缅甸与英国或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的关系时,就有很多不正确的看法和歪曲的论调”。作为一部佛学界和史学界都认为很有价值的南传佛教史及各国公认的缅甸大编年史,《琉璃宫史》讲述了佛教的宇宙观和价值观以及佛教产生、兴起的史实,它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文化和民族关系等无所不包。作为“缅甸人家家户户都应该珍藏的一部充满民族自豪感的历史”,《琉璃宫史》继吴格拉的《大编年史》之后,在缅甸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前夕成功地建构了缅人的国家意识基础,虽未能挽救贡榜王朝,但对缅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强烈的历史自豪感与英国治下的屈辱感及自卑感甚至影响了缅甸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对外关系的需求及取向。
《琉璃宫史》的记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成书时期(公元1829~1833年间) 缅甸的国家思想。当时贡榜王朝第六世王巴基道(即孟概王) 在位(公元1819~1837年),缅甸封建王朝处于盛极而衰的历史转折:随着1769年清缅战争的结束,尤其是1782年孟云王即位后主动与中国改善关系,重视发展本国经济,与暹罗关系趋缓(1807年),缅甸进入了贡榜王朝的“黄金时代”;1819年孟概王即位后缅英关系成为缅甸对外关系的主要问题,1824~1826年第一次英缅战争拉开了贡榜王朝衰落的序幕,直至第三次英缅战争后灭亡(1886年)。而据有关史书推测及本文作者在缅甸曼德勒地区的田野调查,“胞波”用语大约出现于十八世纪末期,而《琉璃宫史》中的缅中“同胞”传说也可视为是对“胞波”的注解。根据缅、中、英多部史书的记载,主持编撰《琉璃宫史》的孟概王算不上治国贤君,但编写历史的努力反映了当时缅甸力求励精图治的期望。虽然《琉璃宫史》1936年才公开出版,但其影响已持续了一个来世纪。因此1948年缅甸恢复独立以后,《琉璃宫史》等经典仍是国家与民族精神塑造的文化基础。
(二) 佛陀的子民
据佛教或历史经典描述,缅甸(古王国) 是有渊源的、不平凡的和荣耀的。《琉璃宫史》按佛教创世说,追溯到大千世界的成、住、坏劫的轮回往返以及宇宙之形成,人类之起源;从众王之首、刹帝利之始祖摩诃三末多的命名、立国写到释迦后裔净饭王之子悉达多王子出家成佛并第一次转法轮为五比丘说法;又从第一次结集写到第四次结集;再从佛音长老赴锡兰取经写到缅甸的阿奴律陀王派人赴直通索取三藏,并在蒲甘乃至全国广建佛塔寺庙,弘扬佛法,进而写到历代缅王如何继承佛教大业,虔敬三宝等。在叙述到缅甸王系时也力图与摩诃三末多王、释迦族系诸王衔接起来,表明缅甸历代君王的始祖源自释迦族,缅甸民众自古就是佛陀忠诚的子民和信徒。在上述宇宙与人类起源、佛教产生及兴起的大背景下,古代缅甸第一王国北缅太公国由太阳王后裔释迦族系的阿毕罗阇王在伊洛瓦底江上游的马垒首建;骠国及后来的古蒲甘国均与太公国及释迦世系有着直接的关联;蒲甘城(阿梨摩陀那) 应佛陀“亲临”预言而在萨牟陀梨王在位期间创建,释迦族太公世系后裔骠绍梯应佛陀授记之言消灭了巨鸟、大猪、恶虎和飞鼯,并以其高贵的王族出生而被列为王储,后成为著名的(古) 蒲甘王国国王“骠绍梯王”,古蒲甘国延绵不断,随着1044年阿奴律陀建立统一的蒲甘王朝,出生“高贵”的缅人国家荣耀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2、骠国乐
作为佛陀的忠诚子民和“天然的佛教徒”,缅甸古代王国尊崇佛陀与佛教,笃信缅甸为神圣的“佛国”。骠绍梯王信守贤人七德,遵循君王十规,皈依佛法,虔敬畏三宝……;笃信佛教的蒲甘王阿奴律陀赴直通(国) 取三藏经典,为使佛教发扬光大,众生受益无穷而亲率大军赴妙香国(中国)奉迎佛牙,从室利差呾罗迎奉佛陀额骨、佛牙并藏于(蒲甘) 瑞喜宫佛塔,在各地修建浮屠、佛窟、寺庙,遣使赴锡兰迎回“化出”之佛牙舍利……经阿瓦/白古王朝(公元1287~1531年),历东吁(公元1531~1752年) 至雍籍牙王朝,从孟云王的“复兴僧伽”到敏董王的“护教扶法”,缅甸佛教均处于“国家宗教”的地位,而1871年敏董王在首都曼德勒举行的“第五届三藏结集”确立了缅甸作为东南亚佛教中心的地位。
(三)骄傲的“帝国”
从历史来看,缅人也在努力塑造一个值得骄傲的“帝国”形象——历史悠久、统一、独立而强大的国家。许多时候,这一“形象”与历史事实存在较大出入,却反映了缅人自身的需要及期待。
一方面,蒲甘王朝为缅人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王朝26的史实已获学界共识,且被编入缅甸国民教育历史教材,另一方面,貌丁昂等缅甸学者宁愿将缅人与“更具进取精神”的骠人联系在一起:虽然缅人出现的时间为公元600年,但缅人在支持骠人并同骠人融合的过程中,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小规模聚居点或王国。而作为以骠人为先行的藏缅人部落,在公元前500多年,佛陀尚在世上之时就从北部进入缅甸,这一时期孟人也从东部进入缅甸。最近,一些缅甸学者也在寻求证实“骠人是缅人之前身”的观点。而根据中国有关民族历史文献,缅(族) 人的先祖(至少一个来源) 源于中国北方,与中国诸多民族在迁徙及现代民族形成过程中有着复杂的关联,例如:公元九世纪初南诏摧毁了缅北的骠国和弥诺国后,治权不达,在缅北形成了一个统治真空,给南下的白狼人一个生存空间。而自七世纪起,以白狼人为主体的民族分批进入(今) 缅甸境内,并在缅甸中部聚集起来。他们融合当地民族,逐渐发展壮大,开始了由白狼人到缅人的转化。在语言上,缅(族) 人为当代缅甸的主体民族(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69%),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彝语支。
作为一部具有“民族主义”特点的作品,缅甸学者貌丁昂的《缅甸史》突出了蒲甘王朝、东吁王朝、雍籍牙王朝等三个由缅人建立的统一的王朝,并称之为“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第三帝国”,这一意图已反映于缅甸当局对“国家英雄”的塑造中——在缅甸国家博物馆、国防博物馆、军事院校等场所的显要位置,均立有标志国家民族精神的阿奴律陀王(蒲甘王朝)、莽应龙王(东吁王朝)、雍籍牙王(雍籍牙王朝) 等三尊塑像。值得注意的是,貌丁昂《缅甸史》中所称之“三大帝国”,均是在与孟、掸、若开等民族政权的战争中开疆拓土并建立的统一的封建国家。而且,东吁王朝及雍籍牙王朝在统一缅地后均发动了对当时中国、泰国的战争,树立了缅人善战的形象,甚至在第一次英缅战争(1824年~1826年) 中,自大的贡榜王朝(雍籍牙王朝) 并不将英军放在眼里,抵抗2年后失败。
3、蒲甘王迎回玉佛
基于历史的交往与交流,《琉璃宫史》的记述反映了缅甸古代王朝对中国“真实”与“虚幻”的认知:神圣的佛教国家,帝王最有权势,有礼仪并讲求正义,人口众多,大臣们充满智慧,老百姓聪明甚至狡诈,物产丰富,信誉良好,拥有布匹等“硬通货”……缅甸史书赞扬中国的目的在于彰显自己“和中国一样伟大”,表明“缅甸并不惧怕中国”,“在谈判中不失尊严”,与中国是“平起平坐”的关系,自然不属附庸。
至于历史上缅甸与中国的关系到底是“贡封(朝贡—封赐) ”还是“平起平坐”?缅甸方面有着一套与中国迥异的话语体系进行解释,这在十八世纪末以来的两国官方交往中可见一斑。自乾隆《大清会典》后,清朝档案文献就将缅甸列为朝贡国,然而缅甸却从未视自己为清朝的朝贡国,甚至一直以一个平等国家的身份与清朝来往。例如,缅方史料记载的《老官屯协议》内容与清朝方面有很大出入,其中的两国政治交往关系,缅甸方面记为“两国每十年互派信使”,清朝方面则记为缅人“缮表入贡”。据清朝档案文献,缅甸基本上每十年朝贡一次,而据缅方文献记载是“每隔十年,清朝先遣使访缅,缅王随之遣使访华”,即缅甸与清朝是“每十年派使互访”的平等国家。据中国史料记载,乾隆五十五年,缅甸再次派出了代表团赴京,中方材料记载为“表贺万寿,贡驯象,请封号”,乾隆皇帝赐敕书、诏书,册封孟云为缅甸国王,并规定贡期为“十年一贡”,中缅形式上的朝贡关系在此时才正式建立。而在贡榜王朝灭亡后,根据英国缴获的缅甸正式文件、档案材料,英国外务部称“据缅甸史书但称馈送中国礼物,并无进贡表文”一事。对比十八世纪末以来缅甸与中国关于两国关系的记载和表达方式发现,缅人往往表现出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特点,态度暧昧,因势而行,同时善用内部话语体系进行解释。作为一个源于“高贵”、以佛为尊的拥有强大武力的统一“帝国”,缅甸最后的王朝——贡榜王朝本质上并未认可对中国之“依附关系”,或者说古代缅甸对与中国关系的自我建构具有独立、平等的特点,其实现“手段”包括自我话语系统的解释、文化想象(如神话传说),必要时甚至发动战争。从另一层面看,古代缅甸与中国交往的基本以及核心的需求是独立、平等。
1886年1月1日,英国完全吞并缅甸并宣布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1937年4月1日后实行印缅分治),骄傲的缅甸“帝国”沦为了“英国殖民地(印度) 的殖民地”,在1948年缅甸恢复独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缅甸陷入深深的屈辱与忧郁之中。与此同时,如此建构起来的国家意识对近现代缅甸精英及执政者及们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缅中“同胞”
(一) 尊贵的“同胞”
据《琉璃宫史》的记述,中国与缅甸同为荣耀的“佛国”,且君王世系始祖共同源于佛陀释迦族乔达摩种系,因而互为“同胞”。据经典所载,释迦牟尼涅槃火化后,香姓婆罗门主持将佛舍利平均分给8位国王……而《缅甸大史》则记载为分给了(包括中国在内的) 11国国王:右上牙分给忉利天国,右下牙分给那伽国,左上牙分给羯陵伽国,左下牙分给了妙香国(对中国的古称) ……其中,“左上牙分给妙香国”仅在有关缅甸经典中记述。“蒲甘王阿奴律陀亲率大军赴妙香国——中国奉迎佛牙”的记载表明缅甸确信中国拥有佛牙舍利,但由于“佛陀并未预言”,“佛牙不肯降于盘中”而未能迎得佛牙,终获天帝释赠玉佛像一尊。天帝释显身对国王(阿奴律陀)说:“佛陀并未预言由汝供奉佛牙,只预言佛法在妙香国长存五千年……”因此,妙香国(中国) 自然也是“荣耀的佛国”。
4、华人抵达伊洛瓦底江边的金多堰
《琉璃宫史》以神话传说及历史记述方式表达了最初的对中国及与中国关系的想象和认知。据记载,“伽拉那伽龙王的孙女,花龙之女赞底来到人间持斋受戒,与太阳神王子有了身孕…… 龙公主将龙蛋产于山边……一枚金蛋在摩谷贾宾一带裂开,变成红宝石矿藏……一枚青蛋漂到妙香国(也说顶兑国或太公国),生出一位公主,公主长大后,被立为王后……一枚白蛋沿着伊洛瓦底江漂到良吴……生出一位神通广大、才智过人、相貌不凡的男孩,即古蒲甘国骠绍梯王……”太阳神之子为人根,出生于尊贵的阿蒂佳太阳族世系,与释迦牟尼佛佛陀同属乔达摩种系——天上的太阳仅能祛除表面黑暗,而太阳神王摩诃三末多王却能祛除内在的黑暗……;“龙”是缅甸帝王及圣者的保护神,修行中的佛陀释迦牟尼得到了龙(那伽) 的保护,著名的古蒲甘王骠绍梯王、蒲甘王朝的姜喜达王等在其孕育、出生及成长中均受到“龙神”的保护。因而,缅、中两国(缅、汉两族) 生为尊贵的“同胞”。
关于《琉璃宫史》的“蛋生”说法,在中国文献和民间传说中均未寻见,这意味着“蛋生”仅是一个缅人的“想象”,即将缅、中两国(两族) 玄妙地描述为基于佛教的拥有神圣的来源及尊贵族源的“同胞”关系。至于“蛋生”传说中所提及的“青蛋”与“白蛋”的性别及颜色深浅的问题,田野调查发现,缅人文化中确有仪式上男性优越于女性,在色彩偏好中浅色优越于深色的说法,但“胞波”一词并不含这些内容,也未见有“同胞”长幼之说。
(二)“同胞”的策略
缅人称呼用语“胞波”背后的“同胞”观,及其在《琉璃宫史》中神话描写的出现并非偶然。单从结果来看,这一概念在文化上为缅甸王国获得“天然”的合法性创造了条件,同时又为其对于中国的独立性与平等性需求作了自我文化注解。
作为强大的帝国,“历史上的中国封建王朝也是周边一些国家或政权合法性的来源——通常是在‘纳贡—册封’的关系运行中实现的”,而缅人对于与中国的关系实质上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策略。缅人经典以宗教(佛教) 为源泉,以神话传说为方式神圣化了与中国的关系——来自“神圣家族”的“血缘同胞”,为在自身话语系统中灵巧回避某些历史时期与中国的“纳贡-册封”问题做了文化铺垫。既是“同胞兄弟”,一方面,具有了与中国的亲密关系及同等地位,同时又是相互独立的个体,非依附性的,而且“兄弟”在文化上是平等的。如此,缅人为在历史经典中否认或回避了与中国王朝某些历史阶段的“藩属”关系或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并为此建构了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的两国关系上看,缅方对于“荣耀”的独立性与平等性的需要及表达与中国王朝对于“进表纳贡”的要求是存在着实质性冲突的,但在特殊的背景下双方都按各自的需要进行解释和记载。缅方的表达,有时温婉,有时则以拒绝“往来”和“纳贡”,甚至武力挑战的方式进行回应。因此,对于同一个事件或协定(如《老官屯协议》),双方各有所表,各得其所。这一关系在十八世纪中至十九世纪初的雍籍牙王朝时期表现尤为突出,甚至反映于缅甸民间称呼“胞波”一词中。
(三) 平等的“同胞”
缅人对于国家独立、平等的需求十分强烈,除了历史的原因及表达,还有其根深蒂固的当地社会文化及宗教基础。缅人社会具有明显的平行、平等以及个人主义的特点。有一句著名的缅语谚语说,“自己主宰自己的世界”——缅人是一个“个人主义”为核心特征的社会,他们珍视并极力维护一个“只属于自我的世界”,并且将这个独处的世界与和他人发生关系的世界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领域;而从家庭关系看,缅人更重视核心家庭——称呼核心家庭成员为“家人”而其他亲属为“亲戚”,兄弟婚后即分别组建自己的核心家庭;在宗教上,“佛教促成了一个平等社会的产生……没有固定的世袭身份划分,没有严格的阶级体系,社会结构中也没有哪一个位置是哪怕最卑微的人不能渴求的”,“佛教告诫民众,每一个个体都与他人平等,每一个个体都只受自己行为的主宰”,人要实现终极解脱却只能依靠自我,“除了自己的心和行为外,没有人可帮助你,即使是佛陀也无法带你证得涅槃,或是送你下地狱……就算有无数的佛,用他们全部的慈悲心,也无法让你脱离苦海,只有你能解脱你自己”。从信仰实践来看,一位佛教徒是通过个人的守戒、修行、布施等努力获取功德的,业报的单位也是个人而不是家庭或其它群体范围,即与其他人无关,哪怕是最亲近的人。这一社会、文化观念及宗教信仰模式对缅人乃至缅人的国家观念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深刻地影响了国内精英、国家领导人乃至国家对外策略。
从古代史籍、近代的民族独立抗争到当代缅甸国家建构,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 人对于国家的独立及与中国“同胞”的平等关系仍然是核心需求。
三、“胞波”的逻辑
如果说《琉璃宫史》中所记述的“蛋生”神话反映了缅人在早期国家意识建构中对于缅中“同胞”观的想象及需求,那么缅人对汉人邻居的“胞波”称呼则是这一概念在特定社会范围的行为表达。缅、汉两族十八世纪末以来在缅甸长期的亲密交往及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共同命运是“胞波”产生及发展的社会基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的缅人对于印度人等的歧视性称呼。“胞波”作为汉、缅两族共同建立的亲密而平等的关系,体现了缅人以“胞波”的称呼为标志的对作为外族(或外国) 人的汉人群体的吸纳,以及在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整合过程。
(一) 缅称“胞波”
随着1769年清缅战争的结束尤其是1782年缅王孟云即位后主动与清廷修好,中缅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战争结束后汉人从陆路进入缅甸者更多,在阿瓦、八莫、孟拱等地都形成了“德祐缪”(中国城),且有战俘2500人羁留缅都阿瓦,从事种植业或其他手工业,并与当地人通婚。“胞波”这个缅人对华侨最亲密的称呼,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使用的。19世纪以来,随着中国(1840年后) 逐渐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缅甸(1825~1886年) 逐渐沦为英国殖民地,中缅两国处境相似,实质性的“中缅交往”主要发生在民间层面,即在缅、汉两族共同的生活中进行。较之于当时英治缅甸对华“留贡”的虚名,“胞波”称呼及两族间的关系更显亲密和平等。《琉璃宫史》中有关佛教、缅人及缅甸早期的记述与古印度诸王国的关系十分密切,但鉴于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缅人的“胞波”称呼仅仅指向来自中国的汉人。
5、敏董王与华人领袖
缅语中,“胞波”(Pauk Phaw) 意为“同一父母所生的兄弟”,其中“胞() ”指“出生”,“波() ”为“一起”,为缅人针对作为非缅人佛教徒的汉人而创造的专用词语,具有如下特点:1.作为“东道主”缅人对“客居者”汉人的亲切称呼,“胞波”所表之“同胞兄弟”并无尊卑之意,仅作长幼修饰,如“胞波基”(老胞波)、“胞波勒”(小胞波) 等,因而“胞波”是缅人对汉人“平等”关系的社会表达;2.明显的感情色彩,为缅人主动使用,意在称呼那些“好的”值得尊敬的汉人,一定程度上具有全族性,为缅、汉两族关系的标志;3.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专属性和排他性,即仅为缅人男性对汉人男性的单向称呼,具有明确的性别特点,不在女性中使用,不用于汉人回称缅人,也不用于缅人间互称,同时对于印度人群体则使用具有歧视性的称呼“格拉”(指外国人),同时也称英国人为“白格拉”(白皮肤的外国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缅语中几乎没有一个专门针对汉人的歧视性词语;4.民间特点,即产生并使用于缅甸民间社会,虽有当时两国友好关系作为背景条件,但“胞波”本身是缅、汉两族民间交往的产物,称呼范围包括整个“德祐”群体,1956年以后也开始指代缅中友好关系。
在社会生活层面,缅人为何主动使用“胞波”称呼他们的汉人邻居而以“格拉”等带有歧视性含义的用语称呼印度人?且不论缅人国家意识与“胞波”在社会层面的关联性,在曼德勒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缅人承认那一时期融洽的缅汉关系,甚至不掩饰对这些“因前世修得好而皮肤白皙”的汉人的好感,同时对这些客居缅甸的汉人有着自己的逻辑:从历史看,缅人是一个“在史书里自豪的民族”;从缅汉社会交往来看,缅人对于这些主要因经济原因(谋生或经商) 远离故土而来的汉人,有着天然的作为“主人”的优越感及“同情心”,凭借丰足的物产,善待这些来自大国的弱势“亲戚”是值得骄傲的或从宗教看是有“功德”的;在当时两国(或两族) 关系友好的情境下,缅人以“胞波”为名接纳这些汉人邻居是适当的,实质上是对汉人的文化整合,而汉人采用缅人亲属称谓称呼对方体现的是于缅人社会的融入;古印度的宗教、历史与文化对缅甸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在英国殖民时代,出于缅甸国家沦为英殖民地甚至是“殖民地(印度) 的殖民地”的屈辱及对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处于强势的英国人及其“仆从”印度人的怨恨,以具有歧视性的称呼“格拉”(外国人) 或“白格拉”(白皮肤外国人) 在观念及社会生活层面对他们进行排斥——“胞波”与“格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 共同的命运与生活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以来,缅、汉两族在缅甸的共同生活中,缅人以“胞波”的称呼接纳了他们的汉人邻居,他们在生计、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亲密交流使得两族文化层面的整合与社会层面的整合实现了统一,两族和睦相处,关系融洽。1886年被英国完全吞并后,缅甸这个曾经的荣耀和骄傲的“帝国”彻底沦为了屈辱的“殖民地的殖民地”(印属印度的一个省),政治、法律、经济、教育文化等完全由英帝国控制。行政上,英印人占据“金字塔”上端,通过与当地封建传统势力结合而直接并完全地控制了缅甸农村基层社会,推行“分治”的民族政策;经济上,英印等资本的疯狂入侵,垄断和高利贷盘剥恶化了缅甸人民的生存状态,且最大的移民群体印度人的涌入,渗透了几乎所有的职业;以培养殖民地行政人员为目的西式教育造成殖民地教育的落后及严重的对外依附性……如此背景下,缅甸社会大致形成了英国人—印度人—缅人(少数民族) —华人的结构,广大缅人与华人在政治、经济上受英印政府及资本的挤压,大致同处“三流”的政治经济地位,缅人与英印人矛盾尖锐,华侨也因此避开了缅甸兴起的民族主义和排外锋芒。近代中缅两国均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和侵略,都开展了反帝运动,缅汉两族互相同情和支持,旅缅华侨也积极支持缅甸人民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如此背景下,缅人与汉人客观上有着“共同的命运”,并在在特定的共同生活中成为了“共同体”。
6、缅皇向华人领袖赐地
生计方式上,往返于中缅之间或定居于缅甸的汉人,大多来自乡村,却较少从事缅人最主要的营生——种植业,而多以手工业、采矿、贸易及辅助性服务行业(如商号、百货店、餐馆、茶店等) 等为主业,与缅人的生计有着较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但十九世纪末大量涌入英印政府治下缅甸的印度人,占据了从政府人员、军人、警察、律师、医生、银行家、工厂主、商人、高利贷者到工人、手工者、农民的几乎所有职业,且同期大量廉价劳工涌入,抢占了底层劳务市场,齐智人高利贷掠夺大量土地,盘剥广大贫困小贩……印度人对缅甸经济的全面“入侵”激起了缅人的抗拒。作为第二大移民群体,“华侨人口仅为印度人的1/10左右”,与印度人不同,华侨与广大缅甸人民得不到支持与保护。
社会生活层面,客居汉人一方面强化内部结构与关系,如建立同乡会、同姓宗亲馆,保持与家乡的联系,另一方面整体被纳入缅甸社会,在缅甸当地的生活中以缅人方式为主,如用缅语,着缅装,熟悉缅人计量规则,遵循当地习俗和制度。虽然族际通婚不是旅居汉人的首选,但由于旅缅汉人人口以男性为主等现实原因,汉人男子与当地缅人通婚的也十分普遍。汉人家庭有着极强的以姓氏为标志的父系继嗣制度及家族观念,而缅人家庭虽然也以父系为主,却无姓氏,生育上并无男性偏好,因此,缅人在与汉人通婚较少出现制度性冲突。例如,汉人男子与缅妻婚后所生的孩子一般男孩随夫姓,接受汉语教育甚至送回国内上学培养,而女孩多随母亲,最终成为“纯粹”的缅人。相比之下,印度人由于宗教信仰及社会组织等原因,与缅甸社会的融入度相对要低。
宗教方面,汉人主要遵循一套基于儒家思想的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综合性的信仰系统,包括“儒教”、佛教、道教以及其它民间信仰的内容,因此对于缅人南传佛教的整合,包括有别于大乘佛教的信仰内容、信仰实践等,是没有障碍的。就缅人观念而言,这些来自中国的汉人本身就是“天然的佛教徒”,而汉人不论是出于生存、信仰还是尊重,与缅甸寺庙的关系十分紧密并愿受寺庙的“监护”。而以穆斯林、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度人,其宗教生活及社会生活相对独立。在缅人的观念里,国家(缅甸)、民族(缅人) 与宗教(佛教) 是一个整体,因而对方是否是佛教徒是个十分重要的标准。缅人对一个外国人最大的期许,即“对于他善行的最好的回报是他来世成为佛教徒,最好是变成缅人佛教徒”。同样,缅人对于族群的认知可以用一座金字塔的形式来表达,在这座族群的金字塔中,缅族佛教徒位于金字塔的最顶端,往下依次是非缅族佛教徒、非缅族非佛教徒、非原住民。按此,汉人应属“第二梯队”,而印度人则属少数民族之后的“外国人”。
(三) 汉人的“胞波”观
对于缅人亲切的“胞波”称呼,作为邻居的汉人并未形成专门的称呼以作回应,也不使用同一用语回称缅人,而以缅语亲属称谓或社会称谓用语称呼缅人的具体角色,如“父亲”“母亲”“叔叔”“哥哥”“儿子”“女儿”或“朋友”等。其实在汉语或汉文化中并无类似缅人的“蛋生”传说,因而缺乏产生“胞波”此类用语的文化基础,在人口数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的汉人使用缅语的亲属称谓来称呼缅人,体现了汉人对缅人社会的融入,也是十分亲切和体现尊重的。这些来自中国的客居汉人,尤其是从陆路经缅北边境而来的“云南人”,一方面努力做得“像缅人一样”,以讲缅话、穿笼基为夸耀,腾冲汉人甚至以“下缅甸”(谋生) 为青年男子的“必修课”,另一方面却保持着根深蒂固的自我文化优越感,但仅表现在汉人群体内部,如华人圈、同乡会、家庭中。
以曼德勒一带的华侨“云南人”为例,客居汉人一方面与缅人共同生活、生计互补、熟悉缅语、信仰佛教,与缅人通婚并关系融洽,另一方面在文化上持守对汉文化及汉语的忠诚。腾冲“云南人”1950年以前虽长期在缅地生活,其生活的重心仍然在中国的家乡,即通过在缅甸的谋生或经商获利,以实现在家乡的家庭理想,如回乡建盖宅子、买田置地、娶妻生子、兴办学堂、支持自己的子孙或同族子弟考取功名。如今在云南腾冲一带,当地汉语方言仍称去缅甸(谋生) 为“下缅甸”,而去省会城市昆明或首都北京(求学或任职) 为“上昆明”“上北京”。在腾冲和顺人及大多数云南汉人的口语中,“上”与“下”不仅是一个表示地势高低或地理方位和方向的用词,而更多表达一个相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概念——从边陲到中心称“上”,从中心到边陲为“下”。对于这些迁自中国内地并久居边疆地区的汉人来说,缅甸属“化外”,自然处于“下方”。“下缅甸”是1950年以前腾冲青年男子的“必修课”,原因多出于无奈,属于“走夷方”的营生。在清代及民国时期流传与腾冲和顺人中的一本被称为“出国必读”的内部手抄本《阳温墩小引》中,也不乏一些针对缅人的歧视性的言语。此外,在表示与缅甸关系时,云南人往往习惯性地使用“滇缅”一词。这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云南人的视野中,自然是用来表示与缅甸地理上的“就近”关系,也含有边地汉人对缅甸的历史认知。在当代区域或国际语境中,“滇缅”可被视为“不对等”甚至对缅甸的“矮化”,如果把习惯的称呼“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放在一起,则会引起缅甸朋友的不适感。
7、广西民族研究
从历史来看,不论中国皇帝如何温柔慷慨,缅甸国王如何宣称不惧“乌底勃瓦”(中国皇帝),也不论民间关系如何亲密,中文文献中记述的中缅关系传统上存在着中心与边缘、朝贡与册封或宗与藩的关系特点,而缅人在其史籍及思想意识中也表现出宗教、历史、现实的骄傲及优越感……在实际的民间交往与交流中,缅人在“东道主”的优越感中“平等”地吸纳客居的汉人,而处境相对弱势的客居汉人则采用内、外两套话语系统进行交流,其中前者仅限汉人内部,格局与家乡无异,包含了对于缅人及缅甸的认知;后者则用于与缅人交往,表现为对缅文化的主动吸收和对缅甸社会的融入,使用与缅人相同的亲属称谓,隐藏了自我文化的优越性及对祖籍地的政治“忠诚”,更多地以良善的实际行动来回应缅人的“胞波”称呼,体现了“和而不同”的观念,营造了两族和谐交往的局面。
四、结语
1950年中缅建交后,两个新兴的邻国共同缔造了新型的现代国家间关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明确体现了两国间独立、平等、和平之精神,终结了两国历史上“贡封”或“平起平坐”此类地位与关系的“纠结”,而“胞波”则被“借用”为中、缅间的专属用语并逐渐成为表示两国友好关系的符号。不论是在缅甸民间社会还是国际关系与政治领域,“胞波”均表相同的含义,其中后者主要在两国间政治场合使用,常用词组包括“胞波情谊”“瑞苗胞波”等,并已作为专门用语在汉语语境中广为人知。缅语语境中有关“胞波”的文化逻辑,由于中缅间事实上的不对称性等原因,仍然深深地影响着当代缅甸对作为表示两国关系用语的“胞波”的理解、情感及态度,并表现于其使用中,且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在文化和政治等领域中呈现出动态的表达。
来源:民族学与人类学
原文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原文编辑 :李建明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孙海梦
《胞波网》编辑:云才
本文系胞波网独家稿件,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paukphaw.net/4164.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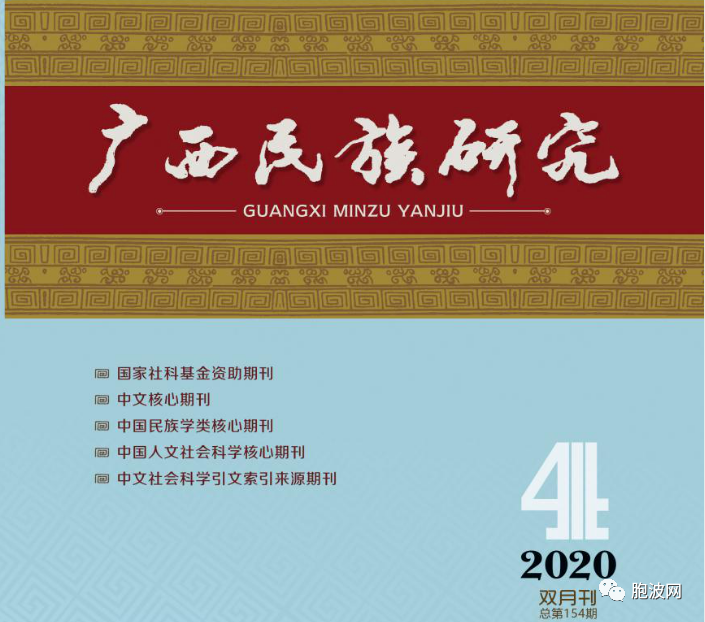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